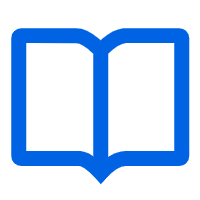五行毅有木吗?
“五行”指的就是金、木、水、火,土。 没有提到“毅”这个字。 所以不存在什么“五行毅”。 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,每个汉字都是一幅画,所以可以通过分析字的构型来判断“字义”的。 “毅”的字形分析如下: 上面是个“广”(房顶),下面是个“辛”字(砍伐树木) ——表示房屋上方的瓦片被雨水冲走了——这当然是不祥之兆!
古人根据这个字形造出“毅”字来象征意味地表达“不祥之事发生了”,以警示后人。 由此可以判断,“毅”的字面意思是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”的意思。 而“雨”字头代表的是“水”,“辛”则代表着“金属”或“刀斧”。 所以“雨辛”合起来的意思就是“遭遇不幸+遇到尖锐物(伤害)”。 这样组合起来之后,“雨辛”就抽象成了带有贬义的词语“悲剧”了。
所以“悲剧”本意就是指“不幸的事件发生了”,而且这种不幸往往伴随着“流血”和“伤害”。 不过现在“悲剧”这个词已经不带任何贬义了,而且还经常用来指代“喜剧”。因为“喜剧”一般都是“不幸事件”造成的,例如《阿Q正传》里就有很多“悲剧性”的结局。
《说文·木部》:“楶(jie),木名也。”郭璞注:“山楸也,又作㮒。”本为一种乔木的名称。段玉裁注引《埤雅》:“楶,楸之木名也。”《埤雅》一书出于宋人陆佃。《尔雅·释木》有“楶,山楸也”。其言“楶,楸之木名也”,是就所读“楶”字本字为“楸”之“木”部而言,若就“楶”字本身而言应说“楸,楶之木名也”。若从“楶,楸”而言,“楸”可以包括“楶”字义,但“楶”却不能包括“楸”字义。《字汇·木部》“楶”旁注为“山楸”,又说:“楶即楸也。”即合《释木》之说而为之注疏。《尔雅·释木》“楶”的注文中既有“楸”字,又有“㮒”字,这是因为字有本字与借字的通假现象。木部有“㮒”字,本是楸木名。《字汇》“㮒”字注为“楸也”。《说文》有“槵”字:“楸也。从木、槑声。”“槢”与“槑”同声,本应从“枿”声才对。木部有“枿”字:“木病出枿,杀上也。从木,叶声。”“枿”与“叶”同声,本字为“䕙”。《说文解字注》:“《本草》作叶。叶,枿之省声。”今汉字省声作捺,读作niě(或作niē、niè)。《字汇》释楶字为山楸,此楶(楸)当为一物。而本为楸木的㮒又作楸的借字,可知“楸”、“楶”、“㭸”、“㮒”、“枿”五字在古时是通假之字。
《说文解字注》:“楶之言枵也。”“枵”字《说文》本无,从《说文》的本字言楶应作㮒枵。枵字从枣声。枣也是乔木名称。《本草纲目·木部·樃枣》:“段成式云:荆楚有樃枣,其实如麦李。今江南有山矾,有青子,圆小如豆,生山中,似枣子。亦一种樃枣。” 樃枣的形状像麦李(即小果子梅),其子生在山上,圆且小,像豆、枣子,也应是木科。楶枵字通,可见也是木楷。张载《老子解》中有“楶橝”,河上公注为“木名也”。橝字《说文》本无,为楸梓之梓的异体字。《方言·木部》有“梓……吴楚之间谓之枌”。枌字《说文》本无,河内《李公岑碑》作“橝”。据此可知,橝为梓枌的形声字,而楸梓,楸枌为楸木,故楶橝与河上公所说“楶枌”同为木名。《墨子·耕柱》:“昔者夏后开使蜚廉、先凯,以伐有易,葆之,而使河冰。天下之民骤鸦。戎师大喜,将必有易。先凯与王刘谋曰:‘胡不抽众甲,使坐于兵车之下。’先凯抽众甲使坐于兵车之下。戎师大溃,禽其将。先凯得有易、河之舟。取鼋、鼍、鱣、鱏,以为天下和。戎师、有易反之,曰:‘有祥起于有易。一男二男,皆乘黑鼋,升天。天雨血三日,夏后开死。’于是乎使飞廉折首、悬羽,以先开。是故民颂曰:‘虞有二姚,后妃是也。何以能之?以胜以巧。何以能胜?辞让以谦。何以能巧?明审以之。’”有易为山川险阻,易水也源出其间。河冰本有易,王刘应为有易国君。夏后使蜚廉、先凯伐有易、河冰之役,同于有夏后开同于后羿。《吕氏春秋·审为篇》有羿使王刘,“王刘,夏之良将也。”《淮南子·人贤篇》也以羿使王刘。刘与刘乃一字之分,王刘应为有易王刘。《吕氏春秋·先识篇》:“有夏后,与有易,战于鸣条之野,后乃身亲冒矢石,矢射王肩,王大怒,还自手射王刘,殪焉,乃反走。有易又射王其中肩,王亦反走。翼请复战,王曰:‘不用人之言至于此。已矣,吾不敢复与天子战矣。’还走,道死于历丘。”(历为同声假借字。历丘应为历山之丘。山有木也。)
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:“羿请不死之药,娥窃之以奔月。妲己斩之以蛊纣。桀乃遂昌帝之尊,倾人不疑。及其亡也,皆曰‘牵乎’,如无与偕焉。故凡任己之智,而不因众人者,恃自之操,而不听忠言,虑患不豫,处治寡恩者,祸福之转也。其反也疾,如以投卵于千仞之谿。”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:“羿死于有娥。”晋褚无量《礼记·注疏·月令,孟秋之月下》注引此《览冥训》《俶真训》之说,也与《吕氏春秋·审为篇》相同言其:“奔月。”其事如《春秋·成公》十六年传:“有狄伐夏后河。”狄戎即王刘、有易族。《孙子·形篇》:“善政者,致人不以远,佐人者,以安、重不争。因而敌之,必以全争于天下,故兵不顿,而利可全。”善用兵者,使敌自至,以逸待劳,乃谓致人。若不如意,则当“因敌之至,故兵不劳而敌困,以佚待劳,此军争之利以全争于天下也。”故曰,致人之术,“不以远”,“佐人者以安”而言。此“安”为“按兵”之义,“安”与“按”同声,从“手”字,“可近可亲”为“近安”,“可近而安之”,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有“九月授衣”之说,是其可“可近而安,可远而亲”,得人也。“可亲而安之,佐人者也。如其不可,则安而示弱,引而不发,此兵家之术,乃使敌自至而图之。故曰,可近则以亲,不可近则使安,致人而不迫,使之自至。虽远不劳,此致人的妙用。“重不争”,所以能“以静制动”,“以逸待劳”。“因而敌之”者,就是“致人”之事,敌人自至而击之,何劳费也?故曰:兵不顿,而利可全。兵顿于敌,敌强而不可敌,则静以待之,引而不发,待其来图之,其术在于“因敌之至。”“以全争于天下”,“以全胜为上也,兵不顿而利可全,以全胜而不以兵顿之患,此争于天下之全者也。有“可近”之,有“可使远亲”之,近者可亲而安之,“可近而亲之,不可近而亲之,可亲而近之”皆可“使亲”,不可亲者,“则安而示弱,引而不发”乃“以静制动”,“以逸待劳”,“虽远不劳”。“可远”之亲者,以安之,亲者以“亲”之,“可远而亲”者,不“争”而“以安”之,“佐人者以安”,此其“不争”的妙用。